经历平远街
经历平远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战史上最贴近今天的团级规模战斗应该是,1992年发生在云南文山砚山县平远街的“禁毒战”。当时动用了三、四千军力将这区域武装对抗的“黄赌毒”一扫而光。有关这事件大家可以在网上查阅。我这里要说的是,我与此地区的人和事打交道的经历。

1985年的秋天,我所在的部队陆军第一师刚刚完成云南老山的轮战,回到驻地杭州。大家都在处理战争后的有关事情,有些乱。一天,营长找到我。说给我一项任务:去云南文山砚山县的平远街,将营里买的录像机退掉;实在退不掉就换台新的回来,但是最好将你的路费也搞回来。——哎!这可不是个好任务。
先说平远街。1984年战前训练时和1985年下阵地后我去过几次。那时我是师直工兵连的副指导员,连队干部分工,我分管十几台装备车辆和司机训练。住地的砚山县听湖酒厂与交通要道的平远街公社没多远,司机训练车辆行驶没多时便到了。有时到这街上停下车,喝点水,逛个街。
这地方真让人迷惑,我脚踏的这土地是不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街上张贴着广告,说的是我这有顶级的毛片;三五成群的一伙人,手腕上带着一串串明晃晃的手表,问你买表不?还有一些手里攥着几把跳刀,问你要刀不?甚至问你要枪不?也有些人手提个油桶,看见军车就爬上驾驶室窗边,要你的油,如果司机同意,他们就拿根管子往车油箱里一放,狠吸一口,用倒虹吸原理将车里的油吸到他们的桶内,然后手腕上摘个手表给司机,换了。他们知道,军车当时供油只登记,不需要出钱,可以随意加。街上店面上各类商品更是让你眼花缭乱,最扎眼醒目的是走私品:彩电、冰箱、录像机……多得很!
当时这是个公社级别的地域,回民占一定比例,是个回族自治地方。公社里党政机构俱全,同时还设立了公安分局这一级别的治安机构,这或许在全国范围内独此无二。
上年纪的人都说那几年乱呀,这平远街应该可称是乱得无以复加!
再说录像机。它是我们刚进入战区的84年8、9月在平远街商店里买的,当时时价为五千多元,有发票在。全营训练后,没什么其他娱乐,就是给大伙放个录像。也算是个精神餐。一个营三个连和一个营部,连轴放,放得勤,放得密;有时还对结了婚的干部们加个“特餐”。这机器没过几个月就糊了,有声音,没图像。当时也不懂,就只认为几千块钱的产品是个伪劣货,必须退换!
这录像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耗损了不少。更要命的是,这用的时间里录像机价格如过山车似的跌去了一半。
这任务分明就是要去混乱之处讲横蛮,还真不容易,还真要点技巧!
几年的军旅生涯,我养成了这样的嗜好:越是特别的、越是困难的任务都想去试试;再加上当时年轻气盛;因此,既然是上级下达的任务,那就必须去执行,也应乐于执行。也只跟营长讲了一个条件:回来时路过长沙准我停留十来天。营长没多少犹豫地同意了。第二天在司务长那借了些路费,开了张营里的《介绍信》,便向云南出发。

两天风尘仆仆的路途,赶到砚山县委招待所住下。当时虽然年轻莽撞,但也没蠢到单枪匹马,逞匹夫之勇地去闯平远街的程度。这平远街再乱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一区域,上级党政部门对他们的发话和指示还有用。臆想好部队高级首长对此事的批示,并写在随行《笔记本》上,什么师长怎么说的,军政委怎么批示的……列了个七、八条。然后去找县委办公室主任。
在一不大的院子里与县委办公室在家的副主任见了面。他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后,就跟我约定第二天与县委常委的宣传部部长详商。
次日按约与部长见面。部长是个读书人,有些文气。虽然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让他分管此类事,但是我们交流相当融洽,有些话点到为止便都明白各自底牌和目的。我装模作样地将“领导们的话”小心道来,他也很顺意地表示:部队首长们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并说,下午你再来,我给你一个解决方案。——应该说我很有分寸地将他唬住了。
下午他给了我个条子,要我去找平远街供销合作社的刘副主任。
随后见到的刘副主任从面相上看就是个诡计多端的狐狸。很显然部长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与他会面后,双方很快进入如何退掉录像机的主题。他率先提出的方案是:我去他那提一台崭新的录像机。我当然地否决了。这是因为,新机子大概已跌到二千二百元左右,虽然可以最低项的满足部队要求,但是与我的心理价位还有些差距。我提出的要求是:全额退还我们购机的五千多块。他当然也不同意。理由是,你用了近一年,而且这一年机子价格跌了这么多。双方僵持着,各讲各的话。但是我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有部长的背书,他一定会让步。
磨蹭一段时间后,刘副主任长叹一声:“唉,干脆你拿二千元走人吧!”
“不行,少得太多了!”我答复他。
“那三千可以了吧?”
我默默地算了算,这可以达到营长对我的中项目标:够买台新的,还够我这次往返的差旅费。于是答复他:“行!”
接着他带着我到财务室领了三千元现金。

那时没有百元大钞,三千元揣在兜里有点鼓鼓囊囊。万元户很少,我怀揣着四分之一还多的万元现金,羡慕死人了!刘副主任默默地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说:“你到我侄儿家去一趟,那里肯定有你想要的好货。”——哈哈,他想将我的现金留在平远街。
我也不傻呀,煞有介事地回复道:“好的,我到厕所去一趟,顺便将钱整理下,也给我的手枪擦擦油,几天没管它了”。说到手枪两字,我还特意地加重了些语气。无非是想告诉他:我有武器在身,危险我不惧。——其实我除了一身军装,什么军用品都没有。
危处不入,乱处不居。还有点轻狂的我不畏危乱。
刘副主任的侄儿一路口等着我。他引我到他家。这是个很气派的房子。虽说不上雕梁画栋,但也有些精雕细琢。一进门穿过客厅到内房,我就惊呆了:二十多台录像机在不停地翻录着,录的是欧美的A片。以最粗鲁的方式生产最低俗的产品。
侄儿引我在更里的一卧室。他在一床下摸出一黑黝黝的二十来公分见方的物品,对我说:“将你那现金留下,将这东西你拿到内地去,保证你翻个几倍。”
“什么吗?”
“鸦片,这东西治肚子痛特别好!”
“你他妈是要老子的命呀!绝对不能干”!我坚决果断地回绝了他。
但是也想想,他带我到这黑窝点,你不买点东西走,他能安心?他能善罢甘休?于是,跟他讲:“我买你两盒磁带吧。”
这磁带也不便宜,两盒用了我三百多块。八十年代的那时顶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了。你可以想象这黑色暴利。
这时,天色已渐渐昏暗。侄儿想留我吃饭。我说已经跟几个朋友约好了在街上一饭店聚餐,推辞了。这地方也没有个让人怀揣“巨款”,也安心的招待所。我对他说,晚上我住他家。让他放心,不再节外生枝。
借晚上街上就餐之机,在街上看了看。猛然发现还有一班从文山到昆明的长途车路过平远街站。我想都没想,一两步窜了上去。车上一看,座位上挤得满满当当的。——不管这个了,图个赶紧离开这危乱之处。走!这趟车是我一辈子最痛苦的乘车记录:从平远街到昆明,在狭窄的汽车车廂里足足站了八、九个小时。
我记得到达昆明时是早上四点左右。我闯进一酒店,要他们给我一间房。他们讲只有过道上的床了。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在那床上躺下,呼噜吹响了几小时!
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终于逃离了危险之地!

一睁眼,立马赶往火车站,买好昆明至长沙的票,第二天就到了长沙。
我的地盘我做主。到长沙的五交化公司买了台新的录像机,这里的价格二千三,还搭送一张彩色电视机票和一台冰箱的票。录像机买下来,电视机家里出钱买了;姐姐准备结婚,冰箱票给了她。就这么干了。
我那少年时的伙伴们一涌而来,坐在我家看录像,也不肯离开。不仅我要递上好茶好水,而且也得搭上好酒好菜,亏死了!其实,他们更多的是等大人上班去之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我这有电视机,录像机,A片,他们的所需所求你应该懂的。
算了算,还有点余钱,可以去买一两盘正规录像带。于是找到同学父亲当领导的湖南金峰音像出版社买了两盘正式出版片。我记得有部片子是苏联二战反思片:《岸》。
十几天很快过去了。我带着录像机等返回杭州部队。录像机交给营里,正规出版片子也交给营里,差旅费也在退款余款中冲销了。后来,营里组织了几次录像晚会。大家说,这个苏联的片子看不太懂。
不过我的任务是可以交差了,应该达到了营长的中项要求。
至于那两盘A片,我将它们做了“糖衣炮弹”,为自己的转业开了路。这个就不详说了。

-

- 《FGO》国服从者图鉴集合
-
2025-04-26 11:34:53
-

- 大张伟:遭大鹏污蔑事业停滞,对方道歉7年,为何他却选择不原谅
-
2025-04-26 11:32:38
-

- 基因帮:在基因测序行业玩起了“电商”,用互联网的力量助力科研
-
2025-04-26 05:56:19
-

- 魂殿如此为祸大陆,为何一直没被其他势力联合围剿呢?原因很现实
-
2025-04-26 05:54:04
-

- 最后一架A380零件抵达图卢兹 史上最大客机“享年16岁”?
-
2025-04-26 05:51:49
-

- 愉妃究竟有何魅力?78岁还被乾隆翻牌子,死后更是被追封为贵妃
-
2025-04-26 05:49:35
-

- 魏桥集团张士平逝世:已完成交接,去年传身体有恙
-
2025-04-26 05:47:20
-

- 孙海英吕丽萍又现迷惑发言,移居美国后心态失衡还是原形毕露?
-
2025-04-26 05:45:05
-

- 花尼姑费贞绫:出家后屡次破佛门清规,她是费玉清的姐姐
-
2025-04-26 05:42:51
-

- 特鲁多终于道歉!“总理之路走到头了”?
-
2025-04-26 05:40:3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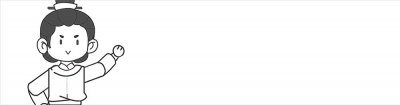
- 吐蕃王朝的兴衰:盛极一时的高原帝国如何最终归于中华大一统?
-
2025-04-26 05:38:22
-

- 团团专访丨带你走近全网爆红的“华农兄弟”
-
2025-04-26 05:36:07
-

- 德云社李鹤东:从“街头混混”,到被郭德纲收为义子
-
2025-04-25 23:26:39
-

- 20部高分战争题材经典电影盘点推荐(一)
-
2025-04-25 23:24:24
-

- 绛珠仙子到底付出了什么?她的财产,才能让贾氏族人有重启的机会
-
2025-04-25 23:22:09
-

- 东北黑帮“教父”——土皇帝刘涌的江湖路
-
2025-04-25 23:19:55
-

- 四大民间故事是哪四个你知道吗?其中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
-
2025-04-25 23:17:40
-

- 1人6证10个名,硬是将自己炒进豪门,诸葛紫岐的手段太高明
-
2025-04-25 23:15:25
-

- 烛之武退秦师的前因后果,名为退,实则引狼入室
-
2025-04-25 23:13:10
-

- 韩红是她的粉丝,歌曲红遍丽江,也困在丽江
-
2025-04-25 23:10:56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